谁敢搞农业民谣?

(本文来源:公众号“音乐天堂”;作者:邱大立)
Folk,在字典里有着下面的划分:民间习俗,民间舞蹈,民间创作,民间传说,民间疗法,民间大会,民间音乐,民间歌手,民间俗话。

当一群群民间的人把镰刀扔到床底,成批地涌进城镇,消磨廉价的盒饭时,他们早已不希罕新鲜粮食的香甜。农业大国这顶已有些老土的帽子再也不是什么光荣的勋章,这时候,“民间”这两个字就已毫不留情地被堆放在一间年久失修并称之为“传统文化”的库房里了,而据一项不完成的统计,它的主人也似乎更乐意对国外游客开放。
最后,“民间”名副其实地化为了冥间。
眼下,全国各地青年都在大搞工业音乐,这种形势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全国人民齐炼钢的火暴景象。炼到最后没材料了,把自己家锅都得抬出来充公。可想而知,炼出来的钢该怎么用。而农业大国炼出来的工业音乐,其质地及性能也是同样令人担忧的。豁出来,拼了!在那开阔得望不到边际的 T恤下,是贫血悲怆发着抖的身子骨。所谓的工业革命,早已变成了一场没有退路的赌博。

某一年给一份报纸作十大女性民谣歌手专题时,才发现,能称之为民谣的女性音乐家实在不多。笔者对一个民谣歌手的定义是十分苛刻的。首先,他(得)自己动脑动笔创作,其次,他(她)得自己会一种乐器。最后,我和做版的那个朋友对着硕大的互联网发了呆:搜遍全球,围来剿去,能符合上述两条指标的竟不到10人。天啊,两位“专家”终于露馅了!在严格的监听情况下,我眼皮都没眨一下,就把Tom Waits的女友Rickie Lee Jones剔了出去。只要一想到她们手里只抓着一个麦克风像个流行歌星那样左拧右荡,我就忍无可忍。

《If I Have To GoTom Waits 》试听链接
她为什么不敢抱一把吉他?
她知道吉他是什么吗?
她知道拨动吉他代表着什么吗?
从目前各种振奋人心的形势看,21世纪的中国似乎已有资格称之为一个准发达国家了。刚从下岗妈妈那里骗到一个月全家生活费换来一件鲜嫩的韩服,然而转身之间就又看到街上下一种更嫩的造型火辣出炉时,一颗颗刚刚平静的心又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。为扮酷而忙得手足无措的孩子们在量身定做自己的包装时,也就是他们最胆战心惊的一瞬。
一个男孩要完成时尚的指标,还要走多远的路?韩服真的让人心寒啊!
《Blowing in the WindInstrumental》试听链接

1997年的MH曾介绍过一位美国女歌手Ani Difranco,从做吉他到创办唱片公司,她都是一个人完成。而时至今日,放眼全球,也没有出现第二例。在一种名叫塔姆布里扎流特琴的古老乐器里,她找到了自己的舌头和语言。她学会了歌唱,那些无知得无法复制的旋律,是简朴花园里衰老的洪水,是清亮之夜里定期的收割。在学校的夜里,她就一遍遍在哼唱着那些古老的歌谣了,在那里,她看到了自己的病容,并知道有一艘船需要修理了。民谣应该是朋友,也是配偶;是敌手,是对手,还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人;是心碎的黄昏,也是忍无可忍的毫无瑕疵;是你下一次富有想象力的迁移,也是灵魂盛宴上狂喜过后的对酒当歌,它还可能是记忆与忘却无数次的搏斗,而对民谣定位最准确的可能就是Ani一首名字奇怪的歌《什么·怎样·何时·何处·为何·是谁》。

就在写这篇文章时,我在一次吃中饭打开电视时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:冬天,在一个湖边,一个人发现一只天鹅双脚冻在了湖中央,他焦急地走了过去。但他很快发现冰开始裂了,他决定滚过去。等到了天鹅身边,他又发现他没有带一件凿冰的工具,怎么办?最后,他花两个多小时用另一种办法凿破了冰:
用哈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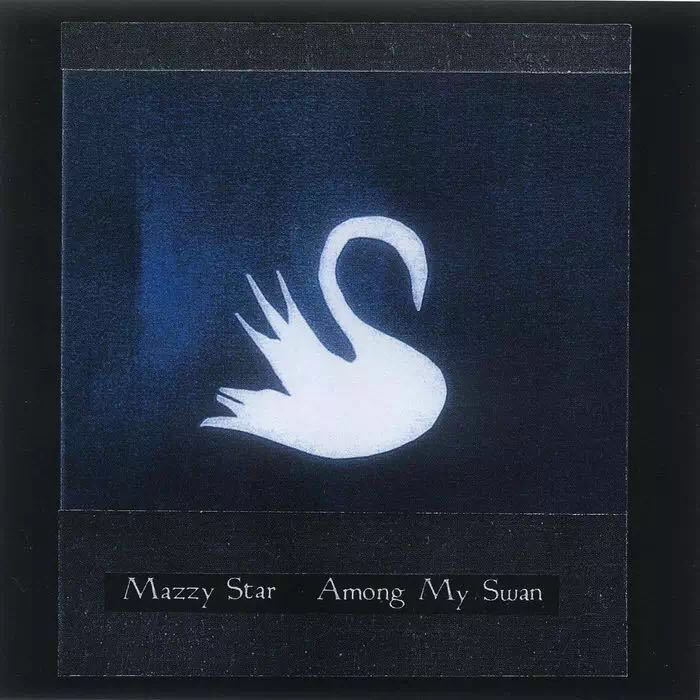
我觉得,这是一首东方版的民谣。当这位中年人一边哈着气一边听着冰块一点点碎裂,而天鹅的鸣叫从渴望、绝望转为希望时,他其实在谱写另一首《天鹅湖》。我觉得,他在那个早上所完成的就是那个冬天里最暖色调的一幅油画。
一个旅顺的青年最大的梦想是搞一次中国乡村音乐节,他听过胡吗个,但觉得胡并非他心中最纯粹的民谣。因为朴素的他听不懂胡的歌词。他说他更想听到杨一的歌。等他好不容易托一个朋友借到杨一的碟准备刻时,却发现碟已放不出了。捧着唱片封套干猜音乐的模样,对一个青年来说多少是一个打击。他是一个推销员,长年累月地提着一包包美发电推子周游全国。出差间隙,他还顺道考察各地的音像市场,碰上处理货就买上几盘。走街串巷时,他也许还幻想说不定能在街头与杨一狭路相逢。但最后,他只发现CC市的警察最傲慢,他不但不回答你的问题,他还觉得你是一个问题。而到了NN市,他一下火车就发觉自己已掉进了一座发廊城,他无法喜出望外,因为他的产品在那些美容院里并不实用。到了GZ市后,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提NN退回来的一箱电推子。他发誓这辈子也不再去NN了。

民谣不了解上流社会,它只熟悉下流社会。于是,民谣应该是体察民意、倾诉民怨的。它不只是锣鼓和唢呐等民乐那么一点点,它应该是最常见的民用公共设施之一。民谣是人民生存质量的一种回答,它不该离人心的标准答案相差太远。民谣其实是人民的心里话在吉他上一种艰难的爬行。在恐怖的体制监控下,很多时代的经典民谣也许只流淌出人民30%的心里话,但30%也比百分之没有要强吧?人是需要音乐的。但是在有些时候,有些场所,有些人民是可以不要音乐的,同时也可以不要喜悦,甚至连哀乐都免了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失去了什么。而所谓的一个个音乐家和艺术家,脱光了也只是一个个虚构或捏造灵魂的人。
而民谣怎么会在这里?

编辑:小楽

全部评论(共0条)
